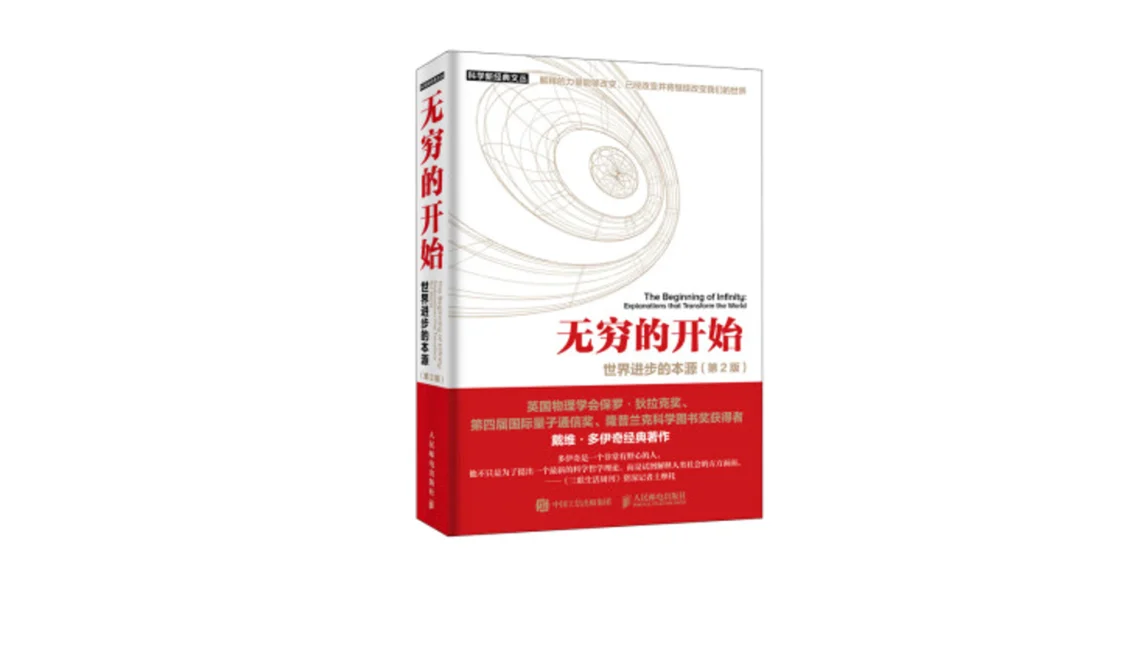大学的自然科学类课程和社会科学/哲学类课程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别:
社会科学/哲学类课程的老师经常要求学生读“经典原著”。哲学老师经常要求读两千年前的柏拉图,社会科学老师经常要求读一百年前的涂尔干,在我们这个向自然科学过渡没多久的心理学里,老师也经常要求学生读弗洛伊德、读威廉詹姆斯、读马斯洛。
而自然科学课程里就极少有这种要求。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大多要学狭义相对论和微积分,但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老师从来不会让学生去读爱因斯坦在上世纪初发表的那几篇著名的论文和牛顿的《流数术和无穷级数》。事实上,连物理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乃至科学家都很少读过这些原典。
多依奇在他的《无穷的开始》里这样写道:“……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所学的全部物理课程,从来没有哪一次是学习从前的伟大物理学家的原始论文或书籍,它们甚至不会出现在阅读列表里。只有当课程涉及非常近期的发现时,我们才会去阅读发现者的著作。我们并不是直接从爱因斯坦本人那里学习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薛定谔、海森堡等,我们也仅仅知道名字而已。我们是从物理学家(而非物理史学家)写的教材中读到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写书的物理学家本人很可能也没有读过先驱者的原著。”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
1.为什么社会科学/哲学类课程需要读经典原著?
——这个角度留给你思考(当然下文中也有间接回答)。
2.为什么自然科学类课程不要读经典原著?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回答。
多依奇在他的《无穷的开始》里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呢?直接原因是,这些科学理论的原始来源几乎从来都不是很好的来源。为什么这样?因为所有随后的阐述都旨在改进它们,有些成功地做到了,改进是会积累的。”
这是自然科学不读原典的第一个原因:科学理论在被提出之后往往会一直得到改进,改进会积累,因此你应该读理论的最新阐释。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提出一种全新理论的人,起初可能还拥有以往理论的许多错误观念。他们需要理解那些理论为什么是有缺陷的、缺陷在哪里,以及新理论怎样解释旧理论能解释的所有事物。但大多数最后来学习新理论的人,关注的东西与此大相径庭。通常他们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个理论,用它来作出预测,或与其他理论结合在一起去理解一些复杂的现象。”
这是自然科学不读原典的第二个原因: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里有很多“历史遗迹”(与旧理论的辩论等等),这些遗迹并不是当代的学习者关心的东西。
最后,最最关键的原因是:
“(当代)科学家们学习一个理论时,对于理论创始人……相信什么并不感兴趣。物理学家阅读一本相对论的教科书时,其直接目标是学习理论,而不是了解爱因斯坦或教科书作者的看法。”
也就是说,理论是独立于理论发明者的喜好、信念的。
“请想象一下,如果历史学家发现爱因斯坦写他的论文只是为了开玩笑,或者是在枪口逼迫下写的,并且实际上他是开普勒定律的一名终身信徒,这对物理学历史将是一个奇怪而又重要的发现,所有教科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都得改写。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本身,物理学课本也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当代哲学研究者需要刻苦研读柏拉图原著,是因为他们想搞清楚柏拉图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当代物理学家其实根本不需要知道爱因斯坦在想什么!
“科学家之所以努力学习一个理论,以及之所以这么不重视忠于原文,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最重要的是,这也是理论创始人的目标。如果它是一个好理论——如果这是一个极其杰出的理论,就像今天的物理学基础理论一样——那么它将极难在仍是一个可行解释的前提下发生改变。因此,学习者对他们的原始猜想进行批评,借助书本、老师和同事的帮助,通过这些手段寻求可行解释,必将得到与创始人相同的理论。理论正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忠实传承下来,尽管完全没有人关心忠实与否。”
多依奇在《无穷的开始》里最终这样总结:
“慢慢地,在经过了许多挫折后,非科学领域里的情形也在朝这一方向转变。”
借用多依奇的这个总结,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在心理学课堂上老师再也不要求学生读弗洛伊德、读威廉詹姆斯、读马斯洛的经典原著,那么心理学那时就算是彻底科学化了。
说明
- 这个“心理学新知小课”系列的文章是当年配合《魏知超:心理学新知课》相关内容而写的科普/杂谈小短文,在已关闭的平台“饭团”上发表,原文链接已不存在。